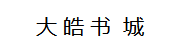撞見江寒和閨蜜接吻后,我利落地提了分手。
他的朋友都賭我最多一個月就會哭著求復(fù)合。
江寒不屑嗤笑:“她哪能等這么久,最多不超過一星期。”
次日,江寒就摟著閨蜜高調(diào)出現(xiàn)在我面前。
他不知道的是,我是真的放下了。
再次見面,我身旁是他的小叔叔。
他臉色大變,質(zhì)問中帶著祈求:“你不是說只喜歡我的嗎?”
1.
朋友說要聚餐。
我匆匆忙忙地從公司趕過來,剛推開包廂門,就看到極其刺眼的一幕。
江寒摟著我的閨蜜蘇靜,笑著向他的兄弟們作介紹。
“來,大家認(rèn)識一下,你們嫂子,蘇靜。”
“那黎渺呢?”有人問。
吃瓜吃到自己身上,我嘲諷一笑,直接推門進入。
一瞬間,包廂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落在我身上。
江寒從容不迫地對上我的視線,微微挑眉,渾不在意道:
“不用管她,我和她已經(jīng)是過去式了。”
“現(xiàn)在,我的正牌女友是小靜。”
距離我和江寒說分手,甚至沒有24小時。
蘇靜得意地瞧我一眼,然后故作害羞地羞紅了臉,躲進江寒的懷里。
若有若無的同情目光落在我身上,讓我滿心難堪。
但凡知道江寒今天會來,我都不會來。
氣氛僵持。
舉辦聚餐的朋友連忙站起來打圓場。
“渺渺你來啦,來,坐我旁邊,我給你點了你最喜歡的草莓啵啵。”
我深呼吸一口氣,不好撫了他的面子,就順著他的臺階下。
來的朋友一大半都是江寒的兄弟。
似有似無的,我不知不覺,就被一群人排除在外。
這倒正合我的心意。
就這樣,一直到聚餐結(jié)束,就行了。
蘇靜卻沒有滿足我這個想法的意思。
她從江寒懷里出來,湊到我面前,火上澆油問:
“渺渺,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?是因為我在這嗎?”
江寒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過來,似笑非笑地看著我:
“看不慣,你可以走。”
我“蹭”地一下從座位上站起來。
見我這樣,舉辦人連忙想要出來打圓場,被我制止。
一次已經(jīng)夠了。
“走當(dāng)然是要走的。”
我居高臨下地盯著江寒兩人,“你們這兩個渣男賤女,我看著就挺倒胃口的。”
頓了頓,我目光又在其他人臉上掃了一圈。
“對我有不滿,麻煩直說,帶著人搞孤立這一套,挺幼稚的。”
說完,我也不管這群人是什么臉色,頭也不回地出了包廂。
但剛走出去幾步,就被追上來的江寒按在肩膀。
他將我抵在墻上,磁性的嗓音中帶著幾分笑意:“真生氣了?”
我沒回答,只是竭力想要將他推開。
江寒右腿向前一步,直接將我的雙腿都抵在墻上。
指尖蹭在我眼尾。
“看你,都難過的要哭了。”
我依然不語,趁著江寒上下其手的時候,手狠狠捏在他腰上,趁他吃痛,將人給推開。
掙脫出來后,我越過他肩膀,看向他身后白著臉的蘇靜:
“管好你的男朋友,別讓他出來逮著人就咬。”
2.
這次江寒沒再追來。
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,我的包落在包廂里了。
我往回走。
剛走到包廂門口,江寒和他兄弟的賭約就傳進了我耳朵。
“寒哥,咋回事啊?你和黎渺真分手了?她不是愛你愛得要死要活的嗎?真舍得和你分手?”
我頓住腳步。
江寒打了個哈欠,就吐出兩個字:“你信?”
“哎呀,我當(dāng)然不信了。”
他的兄弟一陣哄笑,“我賭兩個月,黎渺絕對會在一個月之內(nèi)來找寒哥復(fù)合。”
“你這也太高看黎渺了吧?你忘記大三的時候,黎渺是怎么追我們寒哥的嗎?那舔的,怎么可能需要兩個月,我賭一個月。”
“那我賭半個月。”
江寒不緊不慢的語調(diào)在此刻格外清晰。
“我賭她,最多七天。”
“寒哥你不厚道啊,你這莊家下場,哪里還有我們的活路?”
小丑,一個只是被用來當(dāng)做玩樂對象,徹徹底底的小丑。
我喉頭微動,想說話卻發(fā)不出任何音量。
手臂甚至連開門的力氣都沒有。
下一秒,一只骨節(jié)分明的手替我推開了門。
“好了。”
我下意識地回頭。
出現(xiàn)的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人。
江宴辭。
也是江寒嫡親的小叔叔。
“小叔,你怎么會來這里?”江寒語氣很震驚。
“有點事。”
江宴辭淡淡丟下兩個字,走到舉辦人旁邊的沙發(fā),拿起我的包。
在我還愣神的時候,牽著我離開了現(xiàn)場。
3.
“給你。”江宴辭將我牽出,將手上的包遞過來。
“謝謝小叔。”我感謝道。
江宴辭和江寒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。
他只比江寒大三歲。
但是氣勢,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。
江寒身上雖然有股富二代的痞氣,但身上那股生澀的學(xué)生氣還在。
而江宴辭,渾身下來充斥著屬于上流社會的商界精英的味道。
每次在他面前,我都會有種不敢呼吸的緊張。
和江寒在一起后,我前后也只見過他兩面。
一次是和在路邊,江寒因為有急事,把我一個人扔在了路邊,這位小叔恰好出現(xiàn)。
還有一次是江寒帶我上門見家長,在家宴上。
這是第三次。
在我的印象中,這種身居高位的人,性格都是淡漠,無情的。
完全沒想到,江宴辭,竟然這么“樂于助人”。
嘛,他要是不這么樂于助人,那次在路邊,我恐怕要流落街頭了。
誰讓那時候我手機沒電,身上還沒帶現(xiàn)金。
“和江寒鬧矛盾了?”江宴辭掃了我一眼。
“不是。”我搖搖頭,“我和他分手了。”
“嗯。”他微微點頭,卻完全沒有要放開我包包的意思。
我卻不能當(dāng)什么都不知道。
裝作不尷不尬地甩開。
江寒的電話就時打了過來。
“你跟我小叔去哪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