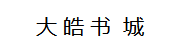還不到三天的期限,父親便等不及了。
因為宮里有人來催,來問大司馬的女兒為何還不進宮,可否是對這門賜婚不滿?
又是一個黃昏,我獨自在廚房煎藥,父親二話不說便沖了進來。
“晚棠,爹對不住你,只是這皇命難違,身不由己。”
我神色淡淡,沉默不語,從容地煎完藥之后便看向了他。
“何時進宮?”
父親剎時眉開眼笑,激動而欣慰。
“有你這樣的女兒,便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。”
我冷笑一聲,在心里翻了一個白眼。
惺惺作態,諂媚虛偽。
父親欣喜的開口。
“入宮時間在十五日后,這幾日你便留在府上學學宮規,然后陪陪你母親。”
我面無表情地應了一聲,然后就端著藥回到了房間。
母親的身子是越來越虛弱了,幾年前因為沒錢看病,舊疾未曾根治的基礎上再患新病,拖到現在連下床都困難。
待我回到房間后,本該躺著的母親卻坐靠在了床上,慈愛而憐惜地望著我。
“晚棠,娘這輩子沒出息,害得你也和娘一起受苦了。”
我用力搖了搖頭,擦去了母親額頭上的汗珠。
“晚棠不苦,從小到大,娘都待晚棠極好,只要能和娘在一起,晚棠就開心。”
然后我用勺子給母親服藥,母親頓了頓,然后開口喝了下去。
“晚棠剛剛去干嘛了?怎么出去了這么久?”
我想到了剛剛和父親的對話,強迫自己笑得自然一點,我還沒把父親要我替楚十鳶入宮的事告訴她,我怕她心里受不住。
“剛剛在院子里摔了一跤,回來的時候便走得慢了些。”
母親有些憂慮地點了點頭。
“磕到哪了嗎?”
我擺了擺手,然后站起來動了幾下。
“瞧,我現在還能活蹦亂跳呢,這府里若是舉辦一個什么運動比賽,我鐵定能獲得名次。”
母親無奈地看著我笑。
“好了,沒傷著就好。”
緊接著,我繼續將藥往母親嘴里喂。
母親先是看著這藥但笑不語,隨后又將我喂的藥喝完。
待我拿著藥碗轉身走到木桌邊時,母親想要說些什么,張了張嘴,卻又沉默了。
借著月色昏黑,娘看不清我眼中的淚花,我輕輕地開口。
“城西懸醫閣又來了一位醫術高明的大師,且等明日一早我便去為娘尋醫,娘一定會健康長壽的。”
母親但笑不語,然后摸了摸我的頭。
“晚棠,明日別去醫館了,便在這別院陪陪娘吧。”
我用手擦了擦眼睛。
“娘,你的身子再拖不得了。”
母親虛弱地張了張嘴。
“可還記得明天是什么日子?”
怎會不記得呢?這是我深深印在心上的日子。
“是娘的生辰。”
母親似是有些疲憊,微微合上了雙眼。
“前些年的生辰,晚棠都在四處為娘求醫,已許久未和娘一起團聚了,今年娘別無他想,只愿能多看看我的女兒。”
我的聲音微顫。
“好。”
于是第二日一早,我便開始為娘準備些吃食。
說是娘的生辰,但我依稀記得幼時是娘在拂曉之時,便搜刮出她僅余的銅錢,精心購置我喜歡的吃食。
無論多貴,無論天氣多么惡劣,只要我想吃,她便是砸鍋賣鐵,挨餓受凍也要為我買來。
現在娘躺在床上行動不便,該換我為她做些什么了。
娘見我忙前忙后,打心底里感到欣慰,那雙溫柔又漂亮的雙眸里淚光漣漣。
這一整天我們都在一起,聊聊往昔,笑笑今朝,而未來如何,我們都在今日暫且放下。
如今我只愿娘能多喚我幾聲晚棠。
可惜我的預感往往是對的,母親如此這般,實是心里早有打算。
那是在她生辰的兩日后,我一早醒來便發現她不在床上。
我慌了神,四處尋找她,未果。
后來只在那張老舊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封信。
她說她自知身體殘破,命不久矣。
她說這么多年來我為了給她尋醫已經奔波了太久,昂貴的藥費和診療費更是增添了我的負擔。
與其繼續依附著我茍活,不如早些了斷,讓我的肩上少些擔子。
她說她不愿做我的累贅,不愿看著我為了給她求醫而四處奔波,不愿看著我為了付昂貴的藥費而吃些殘羹剩飯。
“別再為了娘而活得那么艱難了,娘不想看到我的女兒只為了給我買成堆的藥而低聲下氣,而是想看到她像同齡姑娘們一樣穿著喜歡的裙子,做想做的事。”
看到這里,我的淚水不受控制地往下掉落。
我發了瘋似的在偏院四處奔走,之后便往司馬府外的邊郊跑去。
母親曾說過,她最喜歡府外邊郊的小河,河水朝東流,東邊是她的故鄉。
我一路狂奔,顧不得凌亂衣裙和未曾梳理的頭發,逆著風跑到河邊。
河邊流水潺潺,剔透見底,有魚兒嬉戲打鬧,有落花飄零其間,卻沒有那個曾溫柔地望著我笑,喚我晚棠的身影。
然后我在河流旁的一塊石頭上看到了那個母親親手縫的香囊。
我跌坐在岸邊,目光空洞的望著前方。
前方景色為何,我一概不知,眸中的光早已泯滅,目之所及是白茫一片。
我的心涼得透徹。
娘,你可知道,晚棠不能沒有你,晚棠從來就沒有把你當成過累贅。
晚棠日夜奔走,尋求良醫,吃這殘根剩飯,一點也沒覺得苦。
晚棠只想與娘一起長長久久地在一起啊。
那日我仿佛失去了知覺一般,不知道在河邊坐了多久,也不知道河水何時浸濕了我的衣裳。
直到深更,我的全身被凍的僵硬之時我也未曾緩過神來,手里死死地捏著那個香囊。
那夜,我記得裴司胤來找我了。
彼時我僵硬地靠在岸邊,像一具木偶一般毫無血色,任憑狂風刮過,流水淌過也一動不動。
裴司胤找到我后,將自己身上的寒衣脫下,輕輕地把我包裹住,于是,一陣淡淡的龍涎香縈繞便在了我的周身。
他身著一襲碧藍錦袍,姿容清冷,光風霽月,便是在這苦寒的深夜,也似那東南美玉,落得昆侖一隅,月光傾瀉而下,良玉純白無暇。
“晚棠。”
我望著河流無動于衷,像是忘記了該如何說話。
裴司胤伸過那只修長白皙的手,低垂著眉眼。
“我來接你回家。”
家?我早就已經沒有家了。
我麻木地任由他拉起我。
但是由于在河邊凍了太久,我的雙腿早已麻木,裴司胤剛拉我起來,我便又差點跌了下去。
裴司胤立即接住了我,然后輕嘆了一聲,將我背在了背上。
裴司胤的背上暖暖的,要是換作平時我恐怕會偷偷臉紅幾個日夜,但是現在我滿心滿眼都是我娘永遠的離開我了。
一路上,裴司胤步伐很快,到司馬府的時候,我的淚水早已浸濕他的錦袍。
剛踏進司馬府,楚十鳶便十分焦急地來門口迎接。
她身著淺粉襦裙,烏發雪膚,櫻唇粉腮,面似芙蓉,眉似柳。
“阿晚!爹爹不許我出門,只許我在這門口候著,我擔心你,便叫司胤去河邊尋你,可算是找到了,你還好嗎?”
我勉強地朝她點了點頭,她便立刻叫裴司胤背著我回房間。
回到房間后,楚十鳶摸了摸我的額頭,焦急之色浮上眉間。
“阿晚,你發燒了,我去請郎中。”
我躺在床上搖了搖頭。
“十鳶,我身子骨好,不必請郎中了,我躺一躺便可。”
“我只是,有點難過。”
楚十鳶緊緊地抱著我。
“阿晚,你還有我。”
裴司胤在一旁站著,而我在楚十鳶的懷里默不作聲。
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可笑。
前半生過得與婢女無異,唯一的牽掛也離我而去,我所愛的人喜歡我的姐姐,而我還要替我的姐姐去嫁了那即將駕崩的圣上。
實在是窩囊。